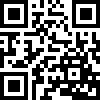□田雪梅
那年夏天,我在北京打工,拿到的第一笔工资,寄给了父亲,并写信让他买一个空调。
父亲在镇上开着家杂货铺。父亲还是个铁匠,于是父亲除了卖货还要帮人家修理一些农具。在夏天,乡下人家要提前拾掇好秋收的农具,钝了的镰刀、豁了牙的铁锹、弯曲的犁铧,一一堆在了父亲的店里。夏日炎炎,烈日最毒时,也是父亲最忙时。父亲挥动大锤,“叮叮当当”,铁与铁之间相接触的刹那,火花四溅;镰刀在磨石来回的打磨下,锈迹斑斑的刀刃终于亮闪如初。父亲光着膀子,脖子上搭条毛巾,当汗如小溪般流下来,辣疼了眼睛,他才拿毛巾擦一下汗。父亲干活时,铺子里热浪翻腾,让人不禁想起太上老君的“炼丹炉”。人还未到门口,便被扑出的热气吓得止住了脚步,父亲挥汗如雨,但对手底下的活儿从未懈怠过。
我打电话询问父亲是否安装了空调,电话那头,父亲愉悦地夸赞着,空调让铺子变成了阴凉房,他在里面干活可自在了。
我上班的地方天天吹着空调,惬意舒畅,想象父亲也能有空调相伴,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。
可没想到的是,表哥出差,顺路来看我。聊起了父亲,他说父亲干那铁匠的活,又热又累,汗淌得太多,人又黑又瘦。迎面碰上父亲险些没认出他来。父亲难道没买空调吗?表哥的话让我心里一惊,我怎么就没想到呢,父亲怎能为了自己舒服,舍得让那个大家伙一天天“吞钱”呢,记得以前父亲说过,空调是吃电的家伙。
“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,你看,你爸托我给你买的什么?”表哥说着,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手机。这是我梦寐以求想要的,但比起父亲的工作环境,父亲更需要空调。父亲用我寄的钱给我买了手机,因为他听说我每次打电话时,都拿着电话卡,到离上班的地方较远的公用电话亭去打。父亲是担心我,心疼我。
那个心爱的手机,我怎么都舍不得用。我托表哥带回去让父亲用,父亲做生意更需要一个随身携带的通信工具。并让表哥带话:我宿舍里装电话了。我的工资涨了,下个月就能买一个手机了。
那天,我又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电话亭,给父亲打电话,父亲呵呵笑着说:丫头,这空调真好用,我正享用着呢,连邻居们都跑来蹭凉了。在父亲美好的描述中,他辛劳的身影又在我眼前变得丰满起来,叮叮当当声中,火星四溅。
我的心痛得厉害,我仰着头,让眼泪倒流回去。泪眼中,我看见的是毒辣辣的太阳,和汗如雨下的父亲。